“归放南山头”——从一幅画谈起
[清]八大山人鸡苗37.8cm×31.5cm
绢本墨笔上海博物馆藏
还记得十几年前,一个文学家跟我说,他去了上海博物馆,看见了八大山人的原作,就是这个我们平常在宣传画册中经常看到的内卷,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他的表情:“好小呀,原以为原著有多大呢,怎么那么小呀!”说话时,还拿手比一下一下尺寸。
我忍着住笑,说:“你没有看八大山人画的鱼吗?也这么小,恐怕比这一只鸡还需要小呢!”
这也难怪,我们已经习惯了国画中最爱表现得这些高大威武的生物,例如猛虎出山,例如气贯长虹,例如战马奔腾……而八大山人画的都是一些小玩意——鱼儿、鸟儿、小猫咪,放到当代又高又大宽阔的艺术馆中,一个不留神,就错过去了。
画一幅《鸡雏》时,八大山人已接近尾70岁,界面可以这么说被八大山人简单化到极致,一只刚从鸡蛋壳中培育出去没多久的小鸡占据着界面中间,孤零零又文文弱弱,除开一首难以相信的诗词和题字以外,都是空缺。有些人说,读这幅作品时,居然陡生这一美术家是不是有些“太狠心”了觉得——这一审美感觉倒真的是奇特。
这幅图尺寸纵37.8cm、横31.5cm,只画上一只小小鸡苗,和八大山人一贯的写意国画又有所不同,反是更贴近工笔画画的画法。细笔勾勒头顶部,神色生动传神;浅墨皴染全身,小细节认真细致,翎毛富有层次感。因此整副著作不仅不是空荡荡,反过来,反是原气充足、张力十足,有点儿像一个好的演员上台、登场,一个器宇轩昂的亮相,压受得了自乱,镇得住场。
因为雏鸡头顶部朝左,仿佛是在向前移动,在这样一个神秘的世界里,它的目光中并没有迟疑、害怕和迷茫。一首五绝题在右上方的块状空缺中,空荡荡背景由于这首诗存有也瞬间充实起来。
我们看一下八大山人写了什么:
鸡谈虎亦谈,德大乃食牛。
芥羽唤僮仆,归放南山头。
这首古诗20个词,没有用一个难字,不知道你看懂了并没有?
即便作为专业科研人员,也可能会问:八大山人在诗里表达什么意思呢?
八大山人一是明朝宗室的流民,讲话务必时刻当心,不可以直表心意;二是曾遁入空门做了禅僧,三十多年的佛法禅学亲身经历,在不立文字、以心传心层面有很大的理解。二者合在一起,让八大山人逐渐形成了表述方式,许多题在画了的诗词、款和印,都像是谜面一般晦涩难懂,交给后代无边无际的猜想与想象。
八大山人的这首古诗,称得上意味着。
最先表述这其中的几个重要历史典故。
“鸡谈”,“谈”哪些?“虎谈”,又“谈”哪些?
南朝宋刘义庆《幽明录》中记了一个故事,说魏晋寡言少语的兖州知州宋处宗获得一只长响鸡,把它放到笼里。有意思的是,这鸡会说实话,它和处宗终日讨论,并且很有见地。宋处宗因而在和他人讨论风水玄学时,语言表达能力大有长进。唐朝的骆宾王《对策文》其三就用到了这些历史典故:“泛兰英于户牖,接座鸡谈;下木叶村于中池,厨烹野雁。”卢照邻《〈南阳公集〉序》也使用这一历史典故:“爱客相寻,鸡谈满席。”这儿的“鸡谈”,就是指“玄谈”“清谈”,谓玄之又玄之话。
大家都熟悉“画饼充饥”这一成语,《二程遗书》中为此来划分“真理”与“常知”,即做为常识的“知”和作为感受的“知”。程颐说,小朋友还会了解虎能够致伤,但人们在一起聊天提到虎时,没人感到恐惧,但是刚好有一位被老虎咬伤过的农民,当她听到有人说到虎时,吓的惊恐万状。八大山人诗中的“虎亦谈”,或来源于此。
第二句“德大乃食牛”,首先看“德大”的意味。《庄子·达生》篇中有一“无所适从”故事:纪渻子为齐宣王养了一只画眉鸟。过去了十天,齐宣王问:“鸡养好了没?”答:“还没有呢,那只鸡目前正飘忽自豪、自视壮气呢。”就这样过去了十天,齐宣王再问。答:“都还没。那只鸡一听见声音就叫做,一见到身影就跳,它心也被外在因素所制约呢。”就这样过去了十天,齐宣王问。答:“都还没。那只鸡依然眼光灵巧,壮气富强。”就这样过去了十天,齐宣王问。答:“嗯,己经养好了。鸡虽然有鸣者,已无变矣,那只鸡看起来就像一只木鸡一样,其德全矣,全部的优秀品质都具备了。其他鸡并没有敢迎战的,都已经被它吓跑了。”充符描绘的那只鸡,便是“全德”之鸡,别的鸡也不敢和它争夺。
第三、四句“芥羽唤童仆”里的“芥羽”,常见于《左传·昭公二十五年》:“季、郈之鸡斗,季氏介其鸡,郈氏为此金距。”孔颖达疏引郑司农曰:“介,甲也,为鸡着甲。”这儿的“介”,是铠甲的意味。《史记·鲁周公世家》引用文献作“季氏芥鸡羽”。裴骃集解引服虔曰:“捣芥子播其鸡羽,能够坌郈氏鸡目。”这儿的“芥”那就不是铠甲,而是把芥子捣烂成粉涂在季氏鸡的身上,两只鸡争夺时,抹了芥粉季氏鸡便会辣到郈氏鸡的眼睛。两种不同的表述,能够共存。后代以“芥羽”指用于争斗鸡。例如应玚的《斗鸡》诗:“芥羽张金距,持续何多彩。”杜淹《咏寒食斗鸡应秦王教》:“卡罗拉初照日,芥羽正生风。”一直到与八大山人与此同时的吴伟业,在《灵岩山寺放生鸡》一诗里还使用这一历史典故:“芥羽狸膏早擅场,争霸身属画眉鸟坊。”
“归放南山头”,是“马放南山”的意味。最开始典出自于《尚书·武成》:“乃偃武修文,归马于华山之阳,放羊于桃园之野,示天底下弗服。”这一历史典故,经常会被用来表示千秋万岁、不会再打仗的含意。
将历史典故一一表述后,再根据八大山人的身世,大概能够做如下的推断:八大山人既不想做一天到晚关起来备受供养的“对谈”之鸡,更不想做一只不可战胜的画眉鸟,希望这一只刚到世界上的小鸡,即不为人的玩具,也远远超过了争夺,理想的归处要在南山头过一种物我两忘、自由的生活。八大山人题完本诗后,刻意盖了“可获得仙人”一印。
将诗中心意思表述结束,回过头再研究一下这一只孤零零的鸡苗,是不是感觉八大山人的书中,对于这个生命拥有无微不至的爱意呢?(文/刘墨)
[免责声明] 本文转载于网络,观点与本站无关。本站不对所包含内容的准确性、可靠性或完整性提供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。请读者仅作参考,并请自行承担全部责任。
文章内容侵权、投诉举报投诉邮箱:Jubao_Times@163.com

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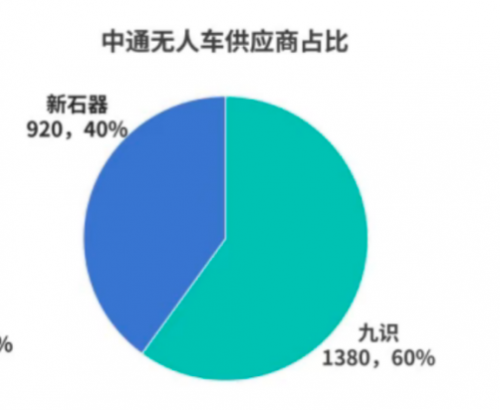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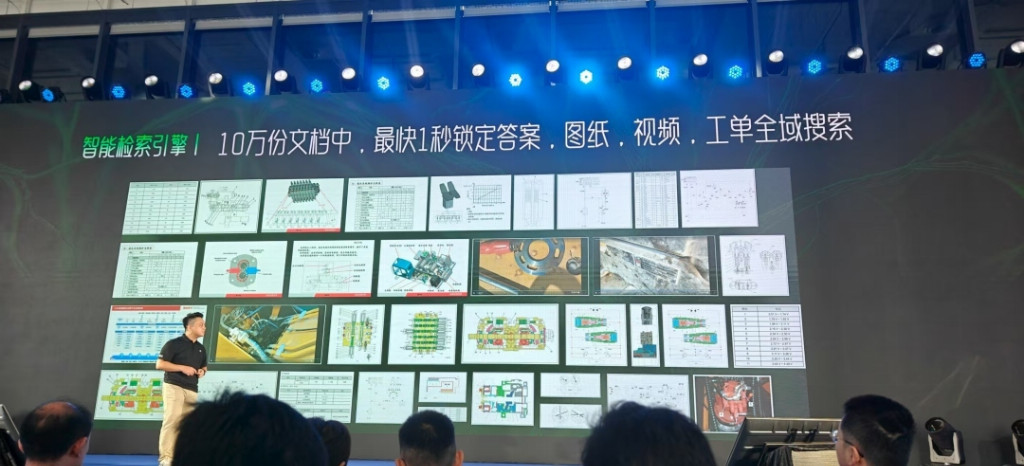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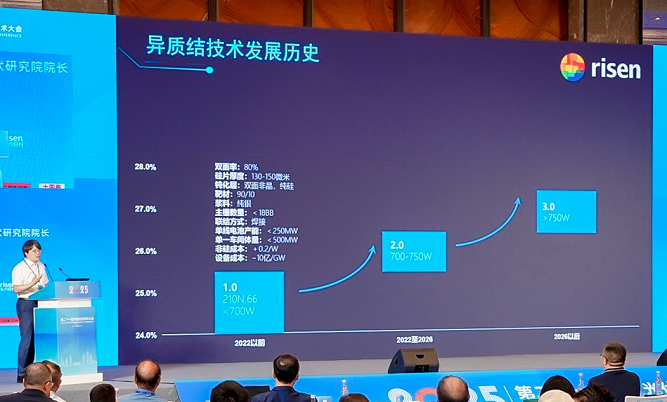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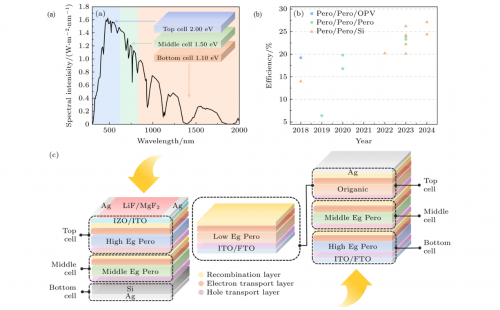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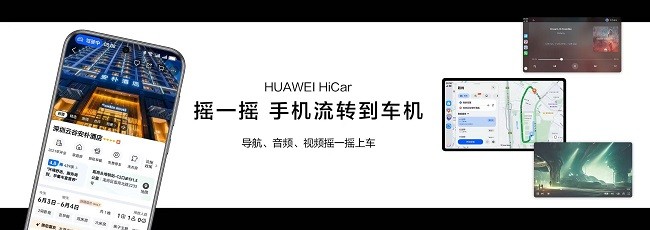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2.6W
2.6W


